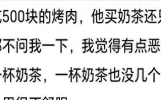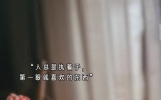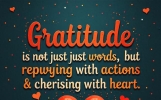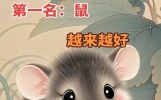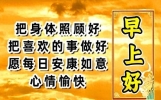爷爷的书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二十多个年轻人挤在一起,笑得眉眼弯弯,爷爷说那是他年轻时的工友,当年每天下班后都要凑在一起喝酒聊天,好得像亲兄弟。
可如今再提起那些人,爷爷只是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后来各自成家、搬去不同的城市,慢慢就断了联系。
现在身边常来往的,也就两三个老伙计。”

我曾以为这是“人情变淡”的遗憾,直到去年冬天,看见爷爷和老周叔、陈爷爷围坐在院子里的火炉旁。
没有喧闹的劝酒,也没有客套的寒暄,爷爷煮着茶,老周叔慢悠悠地翻着烤红薯,陈爷爷则拿着报纸,偶尔念一段新闻。
三个人就这样坐着,沉默的时候也不觉得尴尬,谁渴了就自己倒杯茶,谁饿了就掰一块红薯,阳光落在他们银白的头发上,安静得像一幅画。

爷爷说,年轻时总觉得“朋友多了路好走”,所以忙着参加各种聚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口袋里的名片攒了厚厚一沓,手机里的联系人存了几百个。
可真遇到事的时候,能半夜打电话求助的,始终只有那几个;能坐下来听他说几句心里话的,也不过两三个人。
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明白,朋友多不多,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那些需要费心维持、逢场作戏的“朋友”,不如几个知根知底、相处自在的知己。

就像贾平凹在《自在独行》里写的:“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
人到了一定年纪,不再需要用“朋友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不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的社交上。
与其在喧闹的酒局里强颜欢笑,不如在家泡一壶茶,读一本喜欢的书;与其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小心翼翼,不如和老朋友晒晒太阳,聊聊家常。

前阵子去拜访隔壁的刘奶奶,她退休前是中学老师,桃李满天下。
我以为她的晚年生活一定很热闹,可去了才发现,她的家里总是安安静静的。
每天早上她会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在家写毛笔字,周末偶尔和以前的同事王老师一起去逛书店。
我问她:“您教过那么多学生,怎么不常和他们联系呢?”刘奶奶笑着说:“学生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想打扰他们。
而且人老了,精力有限,能有一两个聊得来的朋友,就很满足了。”
她指着书桌上的书法作品,“你看,我现在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用应付那些不必要的应酬,这样的日子多自在啊。”

我想起自己刚工作的时候,总想着多认识些人,拓展人脉。于是下班后跟着同事去聚餐,周末参加各种行业交流会,可忙忙碌碌了大半年,不仅没交到真心的朋友,还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
后来我慢慢减少了无效社交,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和陪伴家人上,反而觉得生活轻松了很多。
偶尔和大学时的两个闺蜜视频聊天,不用刻意找话题,哪怕只是说说最近的烦心事,也觉得很踏实。

原来人到了一定年纪,朋友越少,生活越好,不是说要封闭自己,而是要学会筛选。
那些三观不合、只懂索取的人,不值得我们掏心掏肺;那些需要我们刻意讨好、小心翼翼维持的关系,不如趁早放下。
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疏远,也不会因为不常聚会而变淡;真正好的生活,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过,不用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不用在喧闹中迷失方向。

就像爷爷和他的老伙计们,不用天天见面,却能在需要的时候互相照应;就像刘奶奶和王老师,不用频繁联系,却能在逛书店时找到共同的乐趣。
人到了一定年纪,终于明白,生活的好坏,不在于身边有多少人陪伴,而在于内心是否自在、是否充实。
朋友少一点没关系,只要都是真心的;日子简单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这大概就是贾平凹所说的“自在独行”,也是人到晚年,最难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