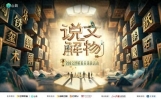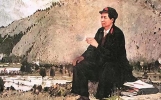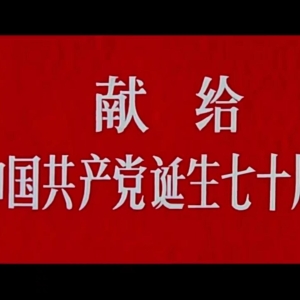提起三国,大家会想起雄心壮志的曹操,想起羽扇纶巾的周瑜,想起忠厚仁义的关羽。三国的精彩,不在于各路英雄豪杰大显身手的英姿,而是朝廷内斗、地方割据的复杂政治格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只记住了英雄,遗忘了那些为谋国家安定、为百姓祈福,冲锋陷阵的人物。
这其中将就有我们经常说的“傀儡皇帝”——汉献帝刘协。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刘协,汉献帝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软弱无能,相反,他是被历史低估的权谋高手。
我们以汉献帝的第一视角,打开被遗漏历史的大门。
九岁登基,朕早懂什么是生存
光熹元年,是朕哥哥刘辩刚上位的第一年。未曾想仅四个月,就发生了宫变。朕至今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的景象:宦官们提着刀在宫里乱砍,何进的人头被扔出宫外,鲜血溅在宫墙上,如同鬼魅般让人心悸。
那时候朕还是陈留王,跟着少帝哥哥在乱兵里逃亡,董卓的铁骑踏碎洛阳街巷的声音,比新年的爆竹更刺耳。
当董卓冲入宫中,提着剑问少帝“事变经过”,哥哥吓得语无伦次时,朕上前一步朗声道:“乱事始末,皆因宦官谋逆。将军勤王有功,何必追问细节?”。当时朕说出这话时,手心的汗已经浸湿了衣袖。
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刀光里护住哥哥,稳住局面,可想而知有多勇敢!
被董卓立为皇帝那年,朕才十岁。朝堂上全是他的人,宫门外都是他的兵。可朕没像后世某些亡国之君那样哭闹,而是每天准时上朝,对着董卓那张肥脸行君臣礼。有人说朕认贼作父,可他们不懂——活下去,才有翻盘的可能。朕悄悄记下哪些大臣敢对董卓翻白眼,哪些将领在军议时面露不满,这些名字,后来都成了朕的暗棋。

衣带诏不是鲁莽,是朕的绝地反击
建安五年曹操把朕迁到许昌,名为定都,实为软禁。朝堂上连咳嗽都要看曹操的脸色,皇后的族人被他随便找个理由就满门抄斩。
朕给董承的衣带诏,不是让他立刻杀了曹操——朕知道那不可能。朕要的是点燃一把火。董承是朕的国舅,手里有旧部;刘备是皇叔,身边有关张;马腾在西凉有铁骑。朕要做的,是让这些反对曹操的力量知道:皇帝还在,皇帝没忘他们。
事情败露后,董承被灭三族,连怀孕的董贵人都被曹操活活勒死。
当时朕知道曹操不敢对我怎样,便对着曹操怒吼:“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曹操再跋扈,也不敢当场杀了朕——杀了朕,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招牌就碎了。
果然,曹操吓得跪地磕头,再也不敢轻易入宫。
而这场“衣带诏”,却被后世笑了千年,说朕幼稚,可谁看懂了朕的布局?
刘备借着“奉诏讨贼”的名义招兵买马,成了曹操最头疼的对手;马超打着“为献帝复仇”的旗号起兵关中,差点端了曹操的老巢。
朕用一场失败的反击,为曹操树了一群死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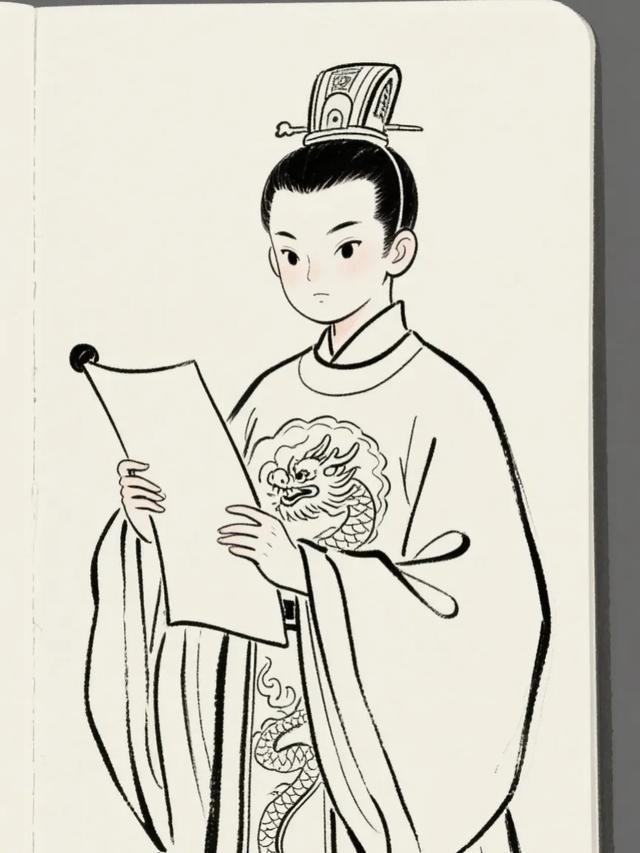
朕的“无为”,是给汉室留的后路
建安十三年,曹操杀了孔融;建安十七年,荀彧被逼自杀;建安十九年,伏皇后被幽禁至死。朕知道汉室气数已尽,可朕不能让它亡得太难看,也不能再让百姓遭受长年战乱之苦。
曹操想当魏公,朕便“诏准”;想称魏王,朕也“亲赐”九锡。朕为了让曹操觉得朕“耽于享乐”,于是便在许昌宫里种了四十株葡萄,每年亲自酿酒。他派来的人看到朕酿酒时的专注,回去禀报“帝无大志”,曹操才能放松警惕。
有人骂朕懦弱,可如果朕拼死反抗,曹操会不会像董卓一样废了朕?换个听话的宗室子弟,那汉室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了。
山阳公的日子,才是朕的清醒
为了大汉人民,此时朕已觉得是时候“告老还乡”。禅位给曹丕那天,朕脱下龙袍换上公服,忽然觉得一身轻松。曹丕封朕为山阳公,给了一万户食邑,还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这话假的可笑,但朕也笑着接受了。
在山阳的十四年,朕才活成了真正的自己。
朕和皇后曹节(曹操的女儿,却始终站在朕这边)一起行医,用宫里学的医术给百姓看病,不收分文。百姓们叫朕“刘公”,孩子们喊朕“先生”,这比在许昌宫里听“陛下万岁”舒心多了。
有一次,曹丕派来的人看到朕在田里劳作,回去说“山阳公乐田园,忘旧业”。他们不懂,朕不是忘,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汉室的血脉。百姓记得刘公的好,就不会忘了大汉曾经的样子。
青龙二年三月,朕在山阳走完了五十四岁的人生。临终前,朕嘱咐葬礼一切从简,不用天子礼。
这不是自轻,是朕明白:真正的能力,不是保住帝位,而是在绝境里守住本心,在大势已去时,给天下人留一点温暖。
后世总说汉献帝是“傀儡皇帝”,可通过了解,我们应该知道:或许,献帝不是什么雄才霸主,但绝不是一个只懂吃喝玩乐的傀儡。
试问:谁能在乱世中活五十四年?谁能让曹操、曹丕都不敢轻易杀朕?谁能让百姓在百年后还念着“刘公”的好?
如果这不算能力,那什么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