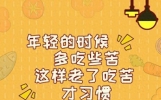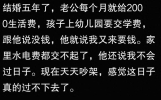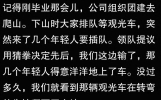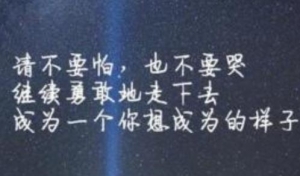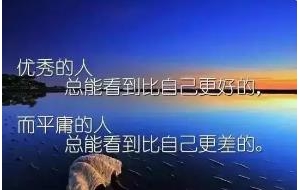康飞
说起来,我与鸡汤的缘分,似乎总是与一些缓慢的、需要等待的时辰联系在一起。

记忆里最真切的一锅鸡汤,是在一个冬日的傍晚。天色早早地沉黯下来,像一块吸饱了墨汁的厚绒布,严严实实地捂住了人间。窗外有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得窗棂子不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屋子里却是一片温存的昏黄,灯早早地开了,光线是那种老旧的、带着暖意的澄黄,洒在厨房冰凉的瓷砖上,也仿佛有了一层毛茸茸的质感。那只母亲惯用的、肚腹圆鼓鼓的紫砂锅,就蹲在煤气灶上,用一身沉静的紫褐,涵养着内里的乾坤。
我是不大去菜场买那种分割好的、冰凉的鸡块的。总觉得那样的鸡,失了魂魄,也便失了熬成一碗好汤的底气。我总要去寻一只完整的、新鲜的鸡,最好是乡间散养的,带着些微泥土与谷物气息的。看着卖鸡的妇人利落地处理,热水烫过,徒手拔毛,那动作里有种世代相传的、不容置喙的笃定。最后,它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皮肤泛着微微的、健康的黄色,静静地卧在塑料袋里,像一件完成了初步雕琢的玉料。
回家,将它请入清水中,细细地、耐心地再次清理每一寸肌肤,特别是那些容易藏匿细绒的翅下与颈脖的褶皱处。这过程,竟有些像一种虔敬的仪式。而后,是“焯水”这关键的一步。冷水下锅,看那水从静止到微微颤动,再到翻涌起无数细小的、乳白色的泡沫,将鸡肉内部的血污与腥气尽数逼出。水面浮起一层浊沫,我用勺子一点点撇去,像为一个新生的生命扫清最初的障碍。捞出的鸡,用热水冲洗干净,通体变得清爽,仿佛卸下了所有尘世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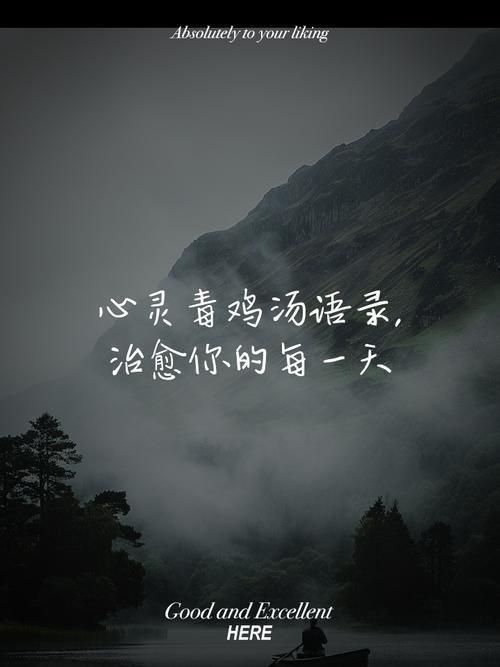
然后,才是真正的开始。将鸡放入那只深沉的紫砂锅,注入满满的、清澈的冷水,拍几块老姜,不加任何多余的佐料,连盐也暂且不放。盖上盖子,开大火。起初,锅里是沉寂的,只能听见煤气燃烧时发出的“呼呼”的低吼。但不久,那沉寂便被打破了。先是锅盖的边缘,开始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白气,像羞怯的试探;接着,那白气渐渐浓郁起来,成了缕缕不绝的游丝;最后,锅盖被水汽顶得“噗噗”地响动起来,这时,便该将火拧到最小,小到只剩中心一朵幽幽的蓝苗。
于是,等待开始了。外面的风似乎更大了,但屋里,只剩下一种极致的“静”。这静,是由那锅持续“咕嘟”着的汤反衬出来的。那声音,细小,绵密,均匀,像春夜里淅淅沥沥的、润物无声的雨,又像慈母在摇篮边哼唱的、无字的眠歌。它不吵人,反倒让周遭的一切都沉静下来。我常常什么也不做,就搬一张凳子,在厨房门口坐下,看着那缕永不停歇的水汽,从锅盖的孔隙中袅袅地升腾起来,笔直地、执拗地,升到半空中,才恋恋不舍地消散开去。空气中,开始弥漫开一种气味。那气味,起初是极清淡的,带着禽类特有的鲜香,渐渐地,它变得醇厚、丰腴起来,像一块无形的、温热的绸缎,将整个屋子温柔地包裹。这气味,是有魔力的,它能让一颗焦躁的心,不知不觉地平和下来。
时间,就在这氤氲的水汽与香气里,被拉长了,也被炖煮得烂熟了。两三个时辰过去,揭开锅盖的一瞬,满屋的香气仿佛找到了归宿,轰然炸开,浓郁得几乎有了形体。锅里的水,早已收敛了最初的张扬,变得沉静而微黄。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金黄色的油花,像秋天午后洒在湖面上的细碎阳光。用勺子轻轻一舀,那汤色是清亮而醇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介于乳白与淡茶色之间的、无比温润的颜色。
这时候,才撒上一小撮盐。盐粒坠入汤中,倏忽不见,只将那鲜味,一下子吊了起来,提了起来,变得立体而分明。盛一小碗,不必用勺,只将碗沿凑到唇边,小心地、试探着呷一口。烫!但紧随其后的,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妥帖。那汤汁滑过舌尖,漫过喉头,一路温暖地滚落进胃里,仿佛一股暖流,瞬间通达了四肢百骸。所有的寒气,所有的疲惫,似乎都在这股暖流里,被融化、被驱散了。你喝下的,仿佛已不只是一碗汤,而是一段光阴,一份耐心,一种被物化了的、名为“慰藉”的情感。
由此,我忽然想到如今满天飞的、被称作“心灵鸡汤”的文字了。它们往往被精心熬制,或者说,被快速冲泡而成。它们有着明确的目标:或激励你成功,或劝慰你放下,或告诉你世间一切美好。它们像一包包速食的汤料,用华丽的辞藻与煽情的故事做调味包,用干瘪的说理做脱水蔬菜,只需读者用眼睛的热水一冲,便能立刻得到一碗看似浓郁、立等可取的道理之汤。
然而,这样的汤,喝多了,是会口渴的。因为它缺少了那最关键的一环——时间。它没有经过文火的、漫长的“咕嘟”,没有在沉寂中与自己对话的过程,没有将血肉与骨骼中的精华,一点点、不情愿地、最终全然交付出去的挣扎与蜕变。它所有的味道,都浮在表面,一尝便知,无法真正滋养人的心灵。

真正能滋养心灵的,或许并非是那些直奔主题的箴言与故事。它也许是午后窗边一缕移动的阳光,在书页上静静走过的痕迹;也许是深夜失眠时,听到的远处传来的一声模糊的火车汽笛;也许是某个黄昏,看见一片梧桐叶,如何挣脱了枝头,旋舞着,最终安然地落回大地。这些瞬间,无用,也无明确的教益,但它们如同熬汤时的火候与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浸润着我们,塑造着我们。
鸡汤的滋味,在于“淡”。而这种“淡”,是从“浓”里化出来的。是将一只鸡所有的风味、所有的经历,都熬煮殆尽后,升华出的一种圆融的、平和的境界。它不企图说服你,更不企图激励你,它只是在那里,静静地,为你提供一份温暖与养分。你喝它,不必思考任何人生大义,只是在那个寒冷的傍晚,你觉得周身暖和了,心也安定了,这便够了。
人之心灵,或许亦如是。那些真正让我们成长的,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与直白的训诫,而是那些说不清来由的、淡淡的欢喜,与无名的惆怅。是这些看似无用的情愫,像文火慢炖一般,将我们的生命,煨煮出属于自己的、复杂的、而后归于纯粹的味道。
锅中的汤,已温凉适口。我端起碗,将最后一点饮尽。窗外的风不知何时停了,夜色显得格外静谧。那碗汤的暖意,已沉入身体深处,而那段炖汤的时光,也仿佛沉淀在了心里,让一切喧嚣,都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