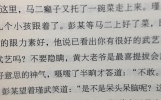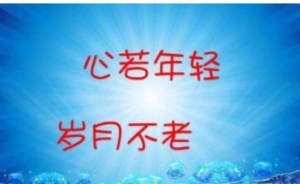1986年春天,南方这个名叫柳溪镇的地方,被连绵的梅雨笼罩着。十八岁的我,顶替退休的父亲,成了镇农机厂的一名学徒工。我的世界,从此被钢铁的冰冷、机油的黏腻和每日重复的流水线作业填满。直到我遇见了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起了毛的《读者文摘》。
它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午休时间。钳工班的老师傅李大海,从他那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衣口袋里,像掏一件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把它摸出来,戴上老花镜,沉浸其中。封面上那个熟悉的、挖掘绿洲的版画图案,与我周围沾满油污的机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鼓起勇气凑过去:“李师傅,看啥呢?”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我平时在车间里从未见过的光:“《读者文摘》,好东西啊。”
那是我第一次借阅。杂志很薄,纸张粗糙泛黄,但里面的文字却像一道强光,劈开了我灰暗的生活。我记得那一期有篇短文,讲的是撒哈拉沙漠里的依米花,用五年的时间扎根,只在第六年开一次小小的花。那一刻,我握着扳手、满是油污的手,微微颤抖了。我偷偷把那篇文章抄在了自己的工作笔记背面。
就这样,我成了这本“流浪杂志”的下一任读者。李师傅郑重地把书递给我,叮嘱道:“小心点翻,别弄脏了,后面还有三十七个人排队等着呢。”
我这才知道,这本杂志属于整个车间。它有一个用硬纸板仔细裱糊的封皮,封底内页,用蓝色圆珠笔画着密密麻麻的“正”字。李师傅告诉我,每传阅一个人,就画上一笔。我数了数,加上我即将画上的那一笔,正好是三十八个“正”字的第一笔——这意味着,它已经被完整地传阅了三十七次。
这本杂志,像一条隐秘的河流,在车间粗糙的外表下静静流淌。它的上游是技术员张姐,一个戴着眼镜、文静的女大学生。每月中旬,她会把新到的杂志带来。首先阅读的,往往是厂办宣传科的“笔杆子”老周,他会用红笔在某些句子下划上波浪线,旁边写上“妙!”或者“深思!”。接着是电工班班长,一个能一边接线一边背诵普希金诗歌的怪才。然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我跟着这本杂志,看到了一个远比车间、比柳溪镇广阔的世界。我读到了爱因斯坦对青年的寄语,知道了有一个叫斯蒂芬·霍金的人在思考时间的起源,读到了来自异国的幽默小品,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存在主义”这个拗口却迷人的词汇。在充斥着“生产定额”、“技改”和“奖金”的日常里,这些文字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氧气。
传阅有着严格的、不成文的规定。每人最多只能保留两天,不能在车间里看(被领导发现会被认为“不务正业”),不能折角,更不能用沾满油污的手直接触碰内页。每次读完,传给下一个人时,我们都会有一种默契的、近乎仪式感的交接。
我记得传给下一个人是翻砂车间的黑娃。他比我大两岁,浑身总沾着洗不掉的黑色砂砾。那天下着小雨,在厂区后墙的拐角,我把用塑料袋包好的杂志塞给他。他黝黑的脸上立刻绽出笑容,飞快地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才接过去,紧紧捂在怀里。“放心,哥,保证完璧归赵!”他呲着一口白牙说。
后来,我在那本杂志的读者来信栏目里,看到了一首署名“柳溪砂工”的小诗,写的是熔化的铁水像奔流的星河。我知道,那一定是黑娃。
这本《读者文摘》我们传阅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张姐调去了市里的总局,新的《读者文摘》断供了。那本传阅了三十八次的杂志,最后传回了李师傅手中,被他锁进了自己的工具箱最底层,成了我们这群人共同的精神秘密。
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农机厂最终在九十年代末改制,工友们星散四方。黑娃去了深圳,从流水线做到了一家电子厂的管理层;李师傅开了个修理铺,手艺闻名乡里;而我,受那些文字的感召,通过业余苦读,考上了夜大,最终成为了一名记者。
2015年,我在省城一家嘈杂的咖啡馆里,用智能手机刷着资讯,享受着信息爆炸带来的便利,却也感到了某种无所适从的空洞。忽然,我接到了黑娃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如今常驻越南管理分厂)。
我们聊起近况,聊起家庭,最后,不可避免地聊到了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黑娃用带着广式口音的普通话,轻轻念道:“‘井底的青蛙,一旦跳出深井,方知天地之广阔。’……哥,你还记得吗?那本《读者文摘》上的话。”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我当然记得。那句话,就抄在我那本早已泛黄的工作笔记上。
原来,那本单薄脆弱的杂志,那些被无数双粗糙的手抚摸过的页面,从未真正消失。它把知识的种子,和看待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深深地埋进了三十八个年轻而饥渴的心灵里。在一個物质与精神都相对匮乏的年代,是它,为我们这三十八个人,撬开了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窗。而我们,也用各自后来的人生,走出了三十八条不同的、却同样坚实的路,回应了那个时代对“知识”最真诚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