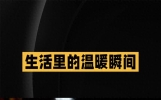“俞任,你今天要是再不去跟隔壁说说,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老婆柳萍把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瞪着我,眼里的火苗子能把天花板点着。
我缩了缩脖子,扒拉着碗里最后两口饭,嘴里含糊不清地应着:“去,去,吃完就去。”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头直打鼓。墙那边又传来了那熟悉的动静,一阵“咚咚咚”的闷响,像是有人在拿橡胶锤不紧不慢地敲墙,中间还夹杂着女人断断续续的、压抑着的哭腔。那哭声挠得人心烦意乱,不是撒泼打滚的嚎,也不是伤心欲绝的恸,更像是那种跑完八百米、累到脱力之后的绝望抽噎。

这日子已经持续了快三个月了。自从隔壁那对小年轻搬来,我们家的安生日子就算到头了。可今晚,当我被老婆逼得没办法,磨磨蹭蹭地走到他们家门口,正准备敲门的时候,我耳朵贴在门上,却听到了一句让我浑身汗毛倒竖的话。而这一切,还得从他们刚搬来那天说起。
说起这事儿,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叫俞任,今年四十二,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里混日子,一个月万把块钱,饿不死也发不了财,图的就是个安稳。我老婆柳萍在商场做个小主管,比我能挣,性子也比我火爆。我们结婚快二十年,日子过得就像一杯温吞水,不好不坏。唯一的念想,就是守着这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安安稳稳地过到退休。
可三个月前,这安稳被打破了。隔壁原来住着一对老夫妻,安静得很,见了面还总笑呵呵地打招呼。后来老两口跟着儿子去国外了,房子空了小半年,然后就来了这对小年轻。

搬家那天动静就特别大,叮里哐啷响了一整天。我从猫眼里往外看,男的叫葛宇浩,高高瘦瘦,戴个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女的叫孙悦,小巧玲珑,看着挺清秀。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模样,郎才女貌,看着挺顺眼。我还跟我老婆说:“挺好,以后邻居是年轻人,有活力。”
结果,我这张嘴就像开了光。活力是真有,就是有点过头了。

从他们住进来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怪事就来了。每天晚上,一到十点钟,隔壁就准时开“交响乐”。起初,我们以为是小夫妻新婚燕尔,干柴烈火,那动静……咳,过来人都懂。我跟柳萍对视一眼,也就笑笑不说话,谁没年轻过?
可这动静一天比一天离谱。除了那让人脸红心跳的床板摇晃声,还夹杂着各种奇怪的噪音。有时候是“滋啦滋啦”像电锯的声音,有时候是“梆梆梆”像木工活,更多的时候,是那种沉闷的、反复的撞击声。最要命的是,几乎每晚后半夜,都能听到那个女孩孙悦的哭声。

柳萍的八卦之火被彻底点燃了。“你说,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不正经的行当?”她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捅我,“我跟你说啊俞任,我白天在楼下碰到王阿姨,她说他们家窗帘一天到晚都拉着,神神秘秘的。”
我翻了个身,不耐烦地说:“人家小夫妻过日子,你管那么多干嘛?说不定是做手工的,晚上赶工呢。”

“赶工?赶工有天天哭的吗?”柳萍不依不饶,“我听着那哭声,八成是家暴!你看那男的,看着斯文,戴眼镜的变态才多呢!不行,你得去看看,万一出人命了呢?”
我被她磨叽得头疼,可一想到要去敲一个陌生邻居的门,质问人家夫妻生活,我就浑身不自在。我这人,脸皮薄,最怕跟人起冲突。于是我就一直拖,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这期间,我们家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柳萍睡眠浅,被吵得神经衰弱,白天上班老打哈欠,回来就冲我发火。我呢,心里也憋着火,晚上睡不好,白天在单位听领导训话都像催眠曲。我们俩因为这事儿吵了好几架,家里的气压比西伯利亚的寒流还低。

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我试过戴耳塞,但那低沉的“咚咚咚”声像是直接从骨头里传进来,防不胜防。我也试过敲墙抗议,结果我这边敲三下,那边静默两秒,然后用更大力气、更快的频率“咚咚咚咚咚”地回应过来,气得我血压都飙到一百八。
最让我起疑心的一次,是上个月的电费单。我们这栋楼,电表都在一楼的电井里。我去交电费的时候,顺便瞥了一眼隔壁的用电量。我的天,足足八百多度!我们家夏天开空调一个月也就四百多度,他们这才刚入秋,用得着这么多电吗?我心里直犯嘀咕,这俩人到底在屋里捣鼓什么呢?难不成真是柳萍说的,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人心就是这样,一旦起了疑,看什么都像证据。我开始留意他们家的垃圾。他们从不自己下楼扔,总是点外卖,然后把垃圾袋放在门口,等保洁阿姨来收。我假装路过,偷偷看过几次,全是泡面桶和最便宜的盒饭餐盒,连点像样的荤腥都没有。按理说,现在的年轻人,就算不富裕,也不至于过得这么寒酸吧?可他们那电费,又完全对不上。

这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一边是老婆的催逼,一边是自己的好奇和烦躁,我感觉自己快被逼疯了。终于,在今晚柳萍下了最后通牒之后,我硬着头皮,像个要去打仗的士兵,悲壮地走到了隔壁门口。
我站在那扇紧闭的防盗门前,深吸了一口气,酝酿着说辞。是先礼后兵,还是直接开门见山?我说:“小兄弟,你们这动静能不能小点?”他要是回我一句“关你屁事”,我该怎么办?是跟他吵一架,还是灰溜溜地回家?

就在我犹豫不决,手抬起来又放下的时候,门里突然传来一句清晰的、带着哭腔的男声:“老婆,对不起……又失败了,这批料全废了……我对不起你……”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男的在哭?不是女的吗?他说什么?料全废了?什么料?
紧接着,是那个女孩孙悦的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哭什么!葛宇浩你是不是个男人!废了就再来!我们从北京辞职回来,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离交货就剩一个月了,哭能哭出钱来吗?起来!把这些废料清了,我们重新和泥!”

这番对话信息量太大,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辞职?投钱?交货?和泥?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跟我脑子里演练了一百遍的“家暴现场”或者“情侣吵架”完全不一样啊!
好奇心彻底压倒了恐惧和尴尬。我鬼使神差地把耳朵贴得更近了。门里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然后是塑料布被扯开的声音,接着,又响起了那熟悉的“咚咚咚”的闷响。
这一次,我听清楚了,那根本不是什么床板声,而是用拳头或者什么软的东西在捶打一大块物体的声音,非常有节奏。而那“滋啦滋啦”的声音,像是一种小型打磨机在工作。

我的心怦怦直跳。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制毒?造假币?还是……就在这时,门突然从里面被拉开了一条缝。
开门的是葛宇浩,他眼圈通红,脸上还挂着泪痕,看到我这个大男人一脸惊愕地贴在他家门上,他也愣住了。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空气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你……你有什么事吗?”他声音沙哑地问,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羞愧。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跟煮熟的虾子似的。偷听人家说话被当场抓包,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我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那个……我老婆说……你们家……动静……”
他一听,脸上的表情更复杂了,愧疚、窘迫、还有一丝绝望交织在一起。他低下头,轻声说:“对不起,大哥,实在是对不起……我们……我们吵到您了。您进来看看吧,看了您就明白了。”

他把门完全打开了。我探头往里一看,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个家!这整个客厅,除了墙角一张铺着单薄被褥的床垫,所有家具都不见了。地上铺着巨大的塑料布,正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地上,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类似橡皮泥一样的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小刻刀、小捏子、画笔、颜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类似油彩和黏土混合的味道。

那个叫孙悦的女孩,正蹲在地上,满手都是彩色的泥,用一把小铲子把一堆已经成型但颜色混杂的泥块铲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的眼眶也是红的,但眼神却异常坚毅。
整个房间,就像一个手工作坊。而那所谓的“噪音”,就是他们工作的声音。那“咚咚咚”的闷响,是葛宇浩在用拳头反复捶打一块巨大的泥团,让它变得更均匀、更紧实。

葛宇浩指着那堆废料,苦笑着对我说:“大哥,真不好意思。我们俩在做……面塑。就是那种传统的捏面人。刚才调色失败了,这一批上千块的材料就都废了,所以……情绪有点失控,吵到您了。”
面塑?捏面人?我愣住了。我印象里的捏面人,不就是公园门口老大爷推个小车,几分钟捏个孙悟空、猪八戒,卖十块钱一个的那种吗?值得他们俩搞成这样?辞职、投钱、又是哭又是砸的?
看出了我的疑惑,孙悦站了起来,擦了擦手,走到墙边一个被白布盖着的大架子前,一把将白布掀开。

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
那架子上,摆满了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但那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小玩意儿!那是一整套《西游记》的人物群像,从孙悟空的金甲、唐僧的袈裟纹路,到猪八戒的憨态、沙和尚的胡须,每一个细节都精致到令人发指。旁边还有一套《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每个人物的表情、兵器、服饰都完全不同,活灵活现,仿佛下一秒就要从架子上跳下来。

这哪里是捏面人,这分明是艺术品!是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那种!
“我们大学就是学这个的,拜了民间的老艺人为师。”葛宇浩的声音充满了自豪,也带着一丝苦涩,“但这个不挣钱,毕业后我们都去了北京的大公司。可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前年,我们师父去世了,他临终前最担心的,就是这门手艺失传。”

“所以半年前,我们俩把工作辞了,拿着这几年攒下的三十万积蓄,回到咱们这儿。房租太贵,我们就租了这儿,把所有钱都投到材料和设备上了。”孙悦接着说,“下个月,市里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我们想带着作品去参展,如果能拿个奖,或许……或许就有活路了。”
我看着他们俩,一个二十六,一个二十五,本该是享受青春、吃喝玩乐的年纪,却把自己关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守着一门快要被遗忘的手艺,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我终于明白了。那巨大的电费,是因为有一台需要恒温恒湿的烘干机,二十四小时不能停。那堆积如山的泡面盒,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时间也没钱好好吃顿饭。那夜夜的“噪音”,是他们和时间赛跑的战歌。那女孩的哭声,不是因为家暴,而是因为一次次失败后的心力交瘁。
我看着他们俩布满老茧和伤口的手,再看看自己因为敲键盘而有些僵硬的手指,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狠狠扇了一耳光。我一个月万把块,过得四平八稳,每天想的是怎么摸鱼,怎么讨好领导,怎么跟老婆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而他们,却在为了一份可能根本没有回报的梦想,燃烧着自己的全部青春。

那一刻,我心里的烦躁、愤怒、猜忌,全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de是巨大的羞愧和敬意。
“对不起……”我发自内心地说,“是我……是我不对,我误会你们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现金——大概有一千多块,全都拿了出来,塞到葛宇浩手里:“大哥也没什么能帮你们的,这点钱,你们拿去……吃顿好的。别天天吃泡面了,身体是本钱。”
他们俩拼命推辞,但我态度坚决。葛宇浩红着眼眶收下了,他说:“大哥,这钱算我们借的。等我们……等我们缓过来,一定还您。”
我摆摆手,仓皇地逃回了家。柳萍看我失魂落魄地回来,立马迎上来:“怎么样?吵起来了没?他们说什么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手机里刚才偷拍的那张《水浒传》群像的照片递给她看。
柳萍起初还不解,当她看清照片里的东西,把图片放大,看到那些人物精妙绝伦的细节时,她也愣住了,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我的天……这是……这是隔壁那俩孩子做的?”

我把刚才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柳萍听完,久久没有说话,眼眶也红了。她默默地走进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锅热气腾腾的排骨汤,又炒了两个菜,装在保温饭盒里。
“给他们送去。”她把饭盒递给我,声音有些哽咽,“咱们……咱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那天晚上,我再次敲响了隔壁的门。当葛宇浩和孙悦看到我提着的饭盒时,他们俩先是愣住,然后,那个一直很坚强的女孩孙悦,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那晚,我们家第一次比隔壁还要安静。我和柳萍躺在床上,第一次觉得隔壁传来的“咚咚咚”的声音,不再是噪音,而是这个城市里最动听的交响乐。我们怕自己这点庸常生活的噪音,会打扰到隔壁那了不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