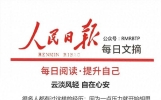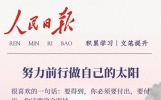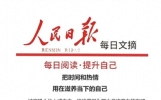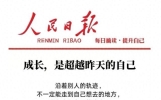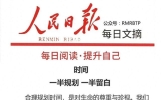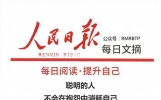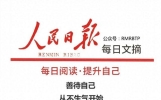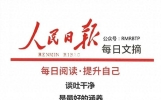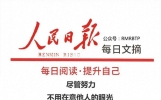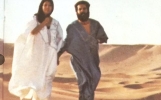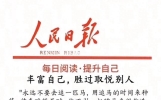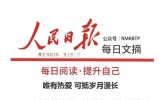“每天15分钟,把自己当一株植物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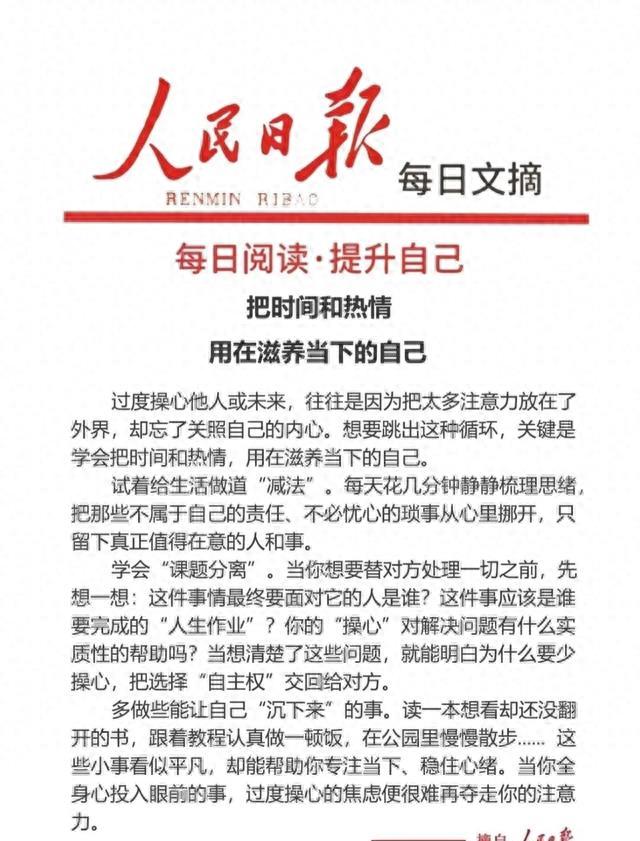
”

刷到这句话时,我正挤在晚高峰地铁里,手机屏幕上是第6条未读工作群消息。
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们像被倒进水族箱的鱼,拼命张嘴却吸不到氧。
哈佛团队去年把36个志愿者关进实验室,只让他们做一件事——每天给自己15分钟“无目的时间”。
有人叠袜子,有人盯着窗外云,有人给多肉擦灰。
三个月后,脑扫描显示前额叶皮层变厚了,焦虑量表得分掉近一半。
听起来像玄学,其实只是把“喘口气”写进日程表。
国内社科院的数字更扎心:78%的人觉得自己被信息活埋,平均一天要在6.2个平台来回切换。
对策不是卸载APP,而是学牧民“转场”——每天固定两小时,手机变板砖。
李娟写《我的阿勒泰》时,记录牧民傍晚“不看羊也不看天,就看自己脚尖”的空白段,城市人照抄作业,把这段空白叫“数字斋戒”。
效果立竿见影:皮质醇降三成,睡眠周期重新对齐。
Z世代把这套玩法升级成“5分钟滋养法”。
等外卖的缝隙,敷张面膜,不刷短视频,专心感受膜布温度从凉到温;
排队买咖啡,不回消息,数奶泡破裂的“噗噗”声,数到第7下刚好叫号;
深夜emo,写三条“今天还不错”的小确幸,写完就关屏,不许复盘。
别小看这几分钟,脑岛叶被反复点亮,人会慢慢长出“自我缓冲垫”。
真正难的是“课题分离”。
朋友失恋,拉你通宵吐槽,你陪到眼底挂血丝,第二天她照样拉黑前任,你却被负能量腌入味。
弟弟考研失利,老妈天天给你打长途,让你“管管”,你硬着头皮劝,回头一看,分数线没涨,你的血压倒飙升。
把别人的情绪还给别人,不是冷漠,是承认:连影子在夜里也会离开,何况成年人的选择。
杨绛在干校养猪时,每天最奢侈的时段是晚饭后关起门,点一盏煤油灯,译《堂吉诃德》。
屋外批斗声此起彼伏,她当背景白噪音。
后来有人问她怎么熬过来,她说:“我只是把一天切成两半,一半给时代,一半给书。
”那半盏灯的疆域,就是她的15分钟,也是她活到105岁的底气。
所以,别再把“爱自己”挂嘴边却约不到时间。
今晚开始,给自己设个“植物闹钟”——
到点就停,像给花浇水,不纠结浇多少,浇了就行;
像树一样,不赶路,只按年轮长大。
三个月后,你未必变富豪,但地铁再挤,心里也留一条通风的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