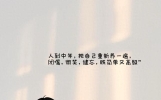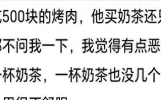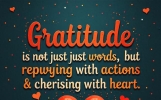老李走的那天,天阴得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灰蒙蒙的,往下拧着潮气。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眼睛眯成两条缝,还是二十来岁时的那个德行。
可我知道,他走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像两座孤零零的山头。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看人的时候,眼神里像是藏着一潭深不见底的水,没什么波澜。
司仪在前面念悼词,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有点失真,嗡嗡地响,像一群苍蝇在我耳朵边上飞。
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些不相干的画面。
我想起我们小时候,趴在村头那条河的堤坝上,看蚂蚁搬家。他指着一队扛着草屑的蚂蚁,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你看,它们这是在娶媳妇儿。
我还想起我们第一次进城,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他非要拉着我去跟一个穿西装的外国人合影。我怂,不敢去。他就自己跑过去,比比划划,最后人家搂着他的肩膀,笑呵呵地拍了张照。照片洗出来,他得意了好几个月。
这些画面,像老旧电影的胶片,一帧一帧地在我脑子里过。
可它们都褪了色,变得模糊,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们上一次好好坐下来吃顿饭,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新开的那个破烂修理铺旁边,有家羊肉馆子味道不错。
我说,忙,改天吧。
这个“改天”,就再也没有来过。
追悼会结束,人群渐渐散了。
我没走,就那么站着,看着那张照片。
他儿子,小石头,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东西。
是个挺旧的铁皮饼干盒子,上面印着牡丹花的图案,边角都磨得露出了铁皮的银白色。
“我爸说,要是他走了,就把这个给您。”小石头的眼睛红红的,声音沙哑。
我接过那个盒子,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
我把它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块冰,那股凉意,顺着我的胳膊,一直钻到我心里去。
回家的路上,我开得很慢。
车窗外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退去。高楼,广告牌,立交桥……这些我每天都看的东西,今天却觉得格外陌生。
这个城市,好像从来没有为谁的离开而停留过。
车里的收音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一个女歌手在里面有气无力地唱着情歌。
我烦躁地把它关掉。
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轮胎压过路面的声音,沙沙的,像时间在流逝。
我把那个铁皮盒子放在副驾驶座上。
它就那么安安静地待着,像一个沉默的谜语。
我突然有点怕。
我怕打开它,看到一些我不想面对的东西。
回到家,老婆给我开了门。
她看我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问:“都……结束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径直走进书房,把门反锁了。
我把那个盒子放在书桌上,盯着它看了很久。
桌上的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光线照在铁皮盒子上,反射出斑驳的光影。
我仿佛能闻到一股时间的味道,是铁锈和灰尘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盒盖。
我犹豫了。
我这辈子,自认为是个果断的人。买房,换工作,投资,我从来没这么犹豫过。
可现在,我却连打开一个盒子的勇气都没有。
我到底在怕什么?
我问自己。
我怕的,或许不是盒子里的东西。
我怕的,是那些被我遗忘的,被我忽略的,被我亲手丢掉的时光。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上刑场一样,猛地把盒盖掀开了。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财宝,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
就是一些……破烂。
一张泛黄的火车票,是从我们老家到北京的。那是我们俩第一次出远门,揣着父母给的几百块钱,说要去首都闯天下。
一个生了锈的啤酒瓶盖。是我们喝的第一瓶啤酒,辣得我们俩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还非要逞强,说这玩意儿比汽水好喝。
半块摔碎了的口琴。他一直想学,可五音不全,吹出来的调子能把人送走。有一次我们俩吵架,我一生气,把他的口琴给摔了。他捡起来,就剩这半块了。
还有一沓信。
信封都黄得发脆了,上面的邮戳也模糊不清。
我抽出一封,打开。
字是他的,歪歪扭扭,像虫子在爬。
“张子,我到北京了。这地方真大啊,楼比咱们村的山都高。我找了个工地搬砖的活儿,一天能挣五十块。你呢?你找到工作了吗?别太累,注意身体。”
落款日期,是二十多年前。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
“张子,我听说你升职了,真为你高兴。我这儿还是老样子,在修车铺当学徒,天天弄得一身油。不过师傅人不错,管吃管住。”
“张子,我谈恋爱了,是个护士,人挺好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说她不嫌我穷。我准备攒钱,回老家盖房子娶她。”
“张zǐ,你结婚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还是我妈听村里人说的。你小子,不够意思。不过还是祝你新婚快乐,早生贵子。我给你寄了点土特产,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张子,我跟她分手了。她家里人不同意,说我给不了她幸福。可能他们说得对吧。我一个人挺好的。”
“张子,我听说你儿子考上重点大学了,真厉害,随你。我开了个小修理铺,什么都修,电视机,电风扇,收音机……生意不好不坏,饿不死。”
“张子,我前两天看电视,看到你了。你在一个什么经济论坛上发言,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真精神。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张子,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去医院查了查,医生说问题不大。你别担心。”
“张子,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最后一封信,没有装在信封里,就是一张折起来的纸。
纸上只有一句话。
“张子,我想你了。”
没有日期。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信纸上,把那歪歪扭扭的字迹,晕染开来。
我像个傻子一样,坐在书桌前,哭得泣不成声。
我老婆在外面敲门,问我怎么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怎么了?
我把一个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给弄丢了。
我脑子里,又开始放电影。
那年夏天,我们俩扒火车去省城。火车开得慢,我们俩挂在车厢外面,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他说,张子,等我们有钱了,就买一辆小汽车,你开,我坐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说,好。
那年冬天,我失恋了,喝得烂醉如泥,躺在马路边上。是他,把我从雪地里拖回去,用热水给我擦脸擦手。我吐了他一身,他也没嫌弃,就那么抱着我,说,没事儿,哥们儿,不就一个娘们儿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说,滚。
那年,我创业失败,赔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我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不敢接电话。是他,揣着他修车攒下的所有钱,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来找我。他把一沓皱巴巴的钱塞到我手里,说,张子,钱没了可以再挣,人不能倒下。拿着,不多,你先用着。
我看着他布满油污的手,和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我说不出一句话。
我拿着他的钱,东山再起。
后来,我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
我换了豪车,住了别墅。
我给他打电话,说,老李,来我这儿吧,我给你安排个清闲的活儿,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算了,我这儿挺好的。
我以为他是跟我客气,是拉不下脸。
我甚至有点生气,觉得他不知好歹。
现在我才明白,他不是不知好歹。
他只是不想用我们的情分,来换取那些他看不起的东西。
他要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钱。
他要的,只是那个能跟他一起扒火车,一起喝闷酒,一起骂娘的哥们儿。
可那个哥们儿,早就在名利场里,迷路了。
我有多久没给他打过电话了?
我记不清了。
每次手机通讯录滑到他的名字,我总会想,等会儿再打吧,现在忙。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的电话,我倒是接过几个。
无非是问我,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儿子怎么样啊。
我总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
忙。开会。有应酬。
这些成了我最常用的借口。
我以为,我们是哥们儿,一辈子的哥们儿,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
我以为,他会一直在那儿,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我从来没想过,他也会老,会病,会离开。
我真是个混蛋。
我拿起那个摔碎的口琴,放到嘴边,试着吹了一下。
发出的声音,嘶哑,难听,像一个老人的哀嚎。
可我却在这难听的声音里,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坐在床边,笨拙地吹着这支口琴,我躺在床上,用一本书盖着脸,假装睡觉。
他吹的,是《同桌的你》。
跑调跑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实在忍不住,掀开书,骂他,你能不能别吹了,吵死了。
他嘿嘿一笑,说,你懂个屁,这叫艺术。
我说,你这叫噪音污染。
我们俩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阳光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那个下午,真长啊。
长得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
盒子底下,还有个东西。
是一个用布包着的小方块。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木雕。
雕的是两个人,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一个是老李。
雕工很粗糙,甚至有点可笑。我俩的脸,都被雕成了鞋拔子。
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因为那个神态,太像了。
那是我们刚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没想到,他却把它刻了下来。
木雕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
“兄弟,一辈子。”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了一下。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一辈子。
他说的是一辈子。
可我呢?
我把他放在了哪里?
我把他放在了应酬之后,放在了合同之间,放在了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之后。
我总以为,来日方长。
可我忘了,人生,是有尽头的。
我把那个木雕紧紧地攥在手里,木头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
可这点疼,跟我心里的疼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二天,我开车回了老家。
我没告诉任何人。
我把车停在村口,那棵我们小时候经常爬的大槐树下。
槐树还在,比以前更粗壮了。
村子变了样,很多老房子都拆了,盖起了二层小楼。
我凭着记忆,往老李家的方向走。
路还是那条土路,只是被来来往往的车,压得更实了。
路边的野草,长得很高,一阵风吹过,哗啦啦地响。
我走到他家门口。
门锁着,一把大大的铜锁,上面已经生了绿色的锈。
院子里的杂草,长得快有人高了。
我能想象到,他最后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
一个人,守着这个空荡荡的院子,守着那些褪色的回忆。
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常常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
他会不会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在他家门口,站了很久。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我去了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条河。
河水还是那么清,可以看见水底的鹅卵石。
河边的芦苇,在晚风中摇曳。
我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
水很凉,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俩在这条河里比赛游泳,看谁先游到对岸。
结果游到一半,我腿抽筋了。
我吓得大喊救命。
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拖上岸。
我俩躺在岸边的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看着天上的白云,说,老李,我刚才以为我要死了。
他说,怕什么,有我呢。你要是死了,我给你捞上来,找个风水宝地把你埋了,每年清明给你烧纸。
我说,滚蛋,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他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河边,传出很远。
现在,他真的走了。
谁来给他烧纸呢?
我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远处的村庄,亮起了零星的灯火。
我走到一座小桥上。
这座桥,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
我们喜欢从桥上往下跳,比谁的胆子大。
我记得有一次,他跳下去,脚被水里的石头划破了,流了很多血。
我背着他,走了好几里山路,才到镇上的卫生所。
他的血,染红了我半边衣服。
我一边走一边哭,我说,老李,你可别死啊,你死了我怎么办。
他趴在我背上,气若游丝地说,放心……死不了……以后……我还要……娶媳妇儿呢……
往事一幕幕,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我靠在桥栏杆上,看着漆黑的河面,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掏出手机,翻开通讯录。
里面存着几百个名字。
客户,领导,同事,合作伙伴……
我滑动着屏幕,一个个名字看过去。
这些人,在我风光的时候,都围着我,张总长,张总短。
可如果我倒下了,会有谁,像老李一样,揣着他所有的积蓄,来拉我一把?
会有谁,在我喝醉的时候,把我从雪地里拖回去?
会有谁,在我快要淹死的时候,拼了命地救我?
一个都没有。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去经营这些人脉,去维护这些关系。
我以为,这些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
到头来,我才发现,我拥有的,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删除的电话号码。
而那个唯一一个,愿意为我拼命的人,却被我弄丢了。
我在桥上坐了一夜。
夜里的风很冷,吹得我骨头缝里都疼。
我想了很多。
想我这前半辈子,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我得到了金钱,地位,别人的羡慕。
我失去了青春,健康,和最重要的朋友。
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
天快亮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回到城里,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司递了辞职信。
所有人都很惊讶。
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事业最顶峰的时候,选择离开。
我没有解释。
有些事,没必要跟别人解释。
我卖掉了市区的别墅,在郊区买了一套小房子。
房子不大,但有个小院子。
我在院子里,种上了花,种上了菜。
我还养了一只狗,是只土狗,我给它取名叫“老李”。
我开始学着过一种慢下来的生活。
我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应酬,不再为了签一份合同而喝到胃出血。
我每天早睡早起,自己做饭,看书,听音乐,遛狗。
我去了很多以前想去,但一直没时间去的地方。
我去看了大漠的落日,去了听了江南的雨声,去了爬了西藏的神山。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给老李写一封信。
当然,这些信,永远也寄不出去了。
我只是想告诉他,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把他那个小小的木雕,放在我的床头。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看它一眼。
它提醒我,我曾经有过一个多么好的朋友。
也提醒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一次,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本相册。
相册里,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
就是那张在天安门广场上,跟外国人拍的。
照片上的我们,那么年轻,那么青涩,笑得那么灿烂。
我们的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我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我仿佛听见,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少年,在对我说话。
他说,嘿,哥们儿,这么多年,你过得开心吗?
我没法回答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被我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回不去的夏天。
后来,我把老李的那个修理铺,重新盘了下来。
我把它收拾干净,挂上了新的招牌。
招牌上只有两个字:“念旧”。
我不会修电视机,也不会修电风扇。
我就坐在那里,喝喝茶,看看书,跟来往的街坊邻居聊聊天。
有人问我,老板,你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说,我这儿,不卖东西,只收故事。
如果你有不要的旧物件,可以拿到我这里来。
如果你有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我说说。
渐渐地,来我这儿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旧东西。
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一个不走了的老座钟,一本翻烂了的小人书……
每一个旧物件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一个叫阿芳的姑娘,拿来一个旧的MP3。
她说,这是她初恋男友送的。里面存的,都是他唱给她听的歌。后来他们分手了,她再也没听过。她想把这个MP3留在我这里,就当是跟过去告个别。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拿来一把磨得光滑的木梳。
他说,这是他老伴儿的。他老伴儿走了十多年了,他每天晚上,还是会拿出这把木梳,对着空气,梳上几下。他说,他怕他老伴儿在那边,没人给她梳头。
我把这些故事,都记在一个本子上。
我发现,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它们就像树的年轮,深深地刻在我们的生命里。
有一天,小石头来了。
他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眉眼间,有几分老李的影子。
他大学毕业了,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
他跟我说,张叔,谢谢你。
我问他,谢我什么?
他说,谢谢你,还记得我爸。
我笑了笑,说,我怎么会忘了他呢。
我们俩聊了很多。
聊他的工作,聊他的生活,也聊他的爸爸。
他说,他以前一直不理解他爸。
他觉得他爸没本事,一辈子就守着个破修理铺,没挣到什么大钱,也没让他过上好日子。
直到他爸走了,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爸留下的,不是钱,而是满满一盒子的情义。
他说,他现在明白了。
人生在世,钱多钱少,其实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没有装着那么几个人。
在你冷的时候,他们会给你披件衣裳。
在你饿的时候,他们会给你端碗热汤。
在你哭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肩膀。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百感交集。
这些道理,我花了五十二年的时间,才弄明白。
而他,这么年轻,就已经懂了。
真好。
送走小石头,我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窗外的夕阳。
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很美。
我想起老李。
我想,如果他还在,看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会说什么呢?
他大概会拍着我的肩膀,咧着嘴笑,说,张子,你小子,总算活明白了。
是啊,我总算活明白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我们拼尽全力,也不过是为了在这世上,留下一点点痕迹。
我们追求名利,追求地位,追求那些看起来很光鲜的东西。
可到头来,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是什么呢?
不是那些冰冷的钞票,也不是那些虚无的头衔。
而是那些,在你生命里,留下过温暖的人。
他们或许不富有,不成功,甚至有些笨拙。
但他们,会用最真诚的心,来对待你。
他们会在你得意的时候,为你由衷地高兴。
他们会在你失意的时候,对你不离不弃。
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多。
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能温暖你的一生。
我拿起笔,在我的故事本上,写下最后一行字。
“老李,谢谢你。也对不起。”
写完,我合上本子,走出门去。
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暖黄色的灯光,洒在我的身上。
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很圆,很亮。
我知道,他在看着我。
我对着月亮,笑了笑。
这一次,是从心底里,笑出来的。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的“念旧”小铺,成了这条街上一个挺特别的存在。
街坊们都知道,这里有个不怎么做生意的老板,喜欢听人讲故事。
他们也乐意把这里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
买菜路过的大妈,会走进来,跟我唠唠今天的菜价。
刚放学的小学生,会跑进来,跟我炫耀他新得的小红花。
失恋的年轻人,会坐在我对面,默默地喝掉一整壶茶,然后什么也不说就走了。
我也不问。
我知道,有些伤痛,需要自己慢慢消化。
我能给的,就是一个安静的空间,和一杯温热的茶。
我的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和宁静。
我不再需要用名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不再需要用酒局来维系所谓的人脉。
我开始有时间,去观察一朵花是怎么开的,一片叶子是怎么落的。
我开始能听懂,风穿过巷子的声音,雨打在屋檐上的声音。
我发现,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进了我的店。
他是我以前生意上的一个伙伴,姓王。
他看到我穿着一身粗布衣裳,坐在一个旧藤椅上,悠闲地喝着茶,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张……张总?真的是你?”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点点头,笑着说:“老王,别叫我张总了,叫我老张就行。”
我给他倒了杯茶。
他局促地坐下,眼睛不停地打量着我这个简陋的小店。
“老张,你这是……体验生活呢?”他试探着问。
我摇摇头:“我这就是生活。”
他更不解了。
“放着那么大的公司不要,跑来开这么个……破店?你图什么啊?”
我看着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我反问他:“老王,你最近睡得好吗?”
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说:“好什么啊,天天失眠。项目,报表,贷款,一闭上眼,全是这些东西。”
我又问:“那你上次,陪你老婆孩子,好好吃顿饭,是什么时候?”
他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不记得了。上个周末,本来答应陪他们去公园的,结果公司一个电话,又去加班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王,我们都一样。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要拼命往前冲,去挣更多的钱,爬到更高的位置。我们以为,那就是成功。可等我们真的爬上去了,一回头,才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挣来的钱,买不回健康。得到的地位,换不来家人的陪伴。”
“我们忙着赶路,却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老王低着头,没有说话。
我能看到,他的眼圈,有点红。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老张,我好像有点明白你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
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只是希望,他明白的那一天,付出的代价,不要像我这么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我又回到了小时候。
我和老李,还是两个光屁股的小孩。
我们俩在河里摸鱼,在田里偷西瓜,在打谷场上打滚。
阳光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我们笑啊,闹啊,好像永远都不会长大。
梦里,他突然转过头,对我说:“张子,你别走了,留下来吧。”
我说:“不行啊,我得去北京,去挣大钱。”
他说:“挣那么多钱干嘛?钱又不能当饭吃。”
我说:“你懂个屁,有了钱,就能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还能住大房子,开小汽车。”
他撇撇嘴,说:“没意思。”
然后,他就转身,跑远了。
我站在原地,想追上去,可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怎么也动不了。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越变越小,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急得大喊:“老李!老李你别走!你等等我!”
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我脸上全是泪。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坐起来,看着床头的那个木雕。
两个勾肩搭背的小人,依旧笑得没心没-肺。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们。
我好像明白了。
老李不是走了。
他只是,把我留在了原地。
他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他让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他让我知道,人生这趟列车,不是开得越快越好。
有时候,停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也很重要。
因为有些风景,错过了,就再也看不到了。
有些同行的人,下车了,就再也遇不到了。
从那以后,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我开始学着,去关心身边的人。
隔壁的刘大爷,腿脚不好,我会帮他把米扛上楼。
对门的王大妈,儿子在国外,一个人过年冷清,我会请她来我家里,一起吃顿年夜饭。
我发现,当我向别人付出善意的时候,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温暖和快乐。
我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一层厚厚的壳包裹着。
它开始变得柔软,变得温暖。
我开始觉得,活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
我的头发,白了更多。
脸上的皱纹,也深了。
但我感觉,我的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年轻。
小石头结婚了。
婚礼上,他请我上台,说几句话。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对笑得一脸幸福的新人,看着满座的宾客。
我有点紧张。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了。
我清了清嗓子,说:
“大家好,我是新郎父亲的朋友,我叫老张。”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我和我最好朋友的故事。”
我把我和老李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从我们小时候一起偷地瓜,到我们长大了各自奔波。
从我们曾经的无话不谈,到后来的渐行渐远。
讲到最后,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说:“我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博取大家的同情。我只是想告诉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年轻人。”
“人生很短,一晃就老了。人生也很长,长到足够让你犯很多错。”
“我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弥补,可以去挽回。但很多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那个愿意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的人。那个你半夜打电话过去,他会骂你神经病,但还是会听你把话说完的人。那个你功成名就了,他不会嫉妒你,只会默默为你高兴的人。”
“这样的人,遇到了,就是你一辈子的财富。”
“不要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最后,祝愿这对新人,也祝愿在座的各位,都能拥有,并珍惜,你们生命中,那个独一无二的真心朋友。”
我说完,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我看到,很多人,眼睛都红了。
我走下台,小石头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说:“张叔,谢谢你。我爸要是听到你这番话,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拍了拍他的背,说:“傻小子,该说谢谢的,是我。”
是我,该谢谢老李。
他用他的生命,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婚礼结束后,我一个人,又去了那条河边。
夕阳西下,河面上一片金黄。
我拿出那半块口琴,放在嘴边,吹起了那首《同桌的你》。
调子,依然跑得厉害。
声音,依然嘶哑难听。
但我吹得很认真。
因为我知道,在另一个世界,有一个人,正在听着。
风,轻轻地吹过我的脸颊。
像是谁的手,在温柔地抚摸着我。
我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
他站在阳光下,对我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他说:“张子,你看,今天的夕阳,真好看。”
我笑了。
是啊。
真好看。
我52岁送走老伙计,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拼凑起他离开的真相,和我自己内心的废墟。
我不再去想那些“如果”。
如果我当初多给他打几个电话。
如果我当初能多去看看他。
如果我当初能早点发现他的病。
这些“如果”,都没有意义。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带着他的那份情义,好好地活下去。
活得像他希望我活的样子。
简单,真实,温暖。
我的小店,还在开着。
故事,还在继续。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某个重要的人。
我们或许素不相识。
但我们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朋友。
他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
他会在我们脆弱的时候,给我们注入力量。
他会陪着我们,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直到我们,也变成天上的星星。
然后,在另一个世界,笑着重逢。
我们会勾肩搭背,像从前一样,说一句:
“嘿,哥们儿,好久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