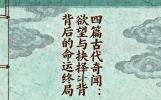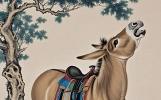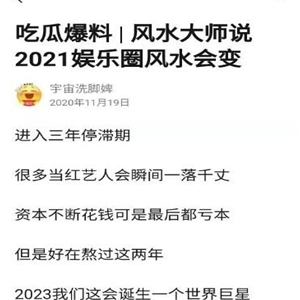乌泷坑里那条怪鱼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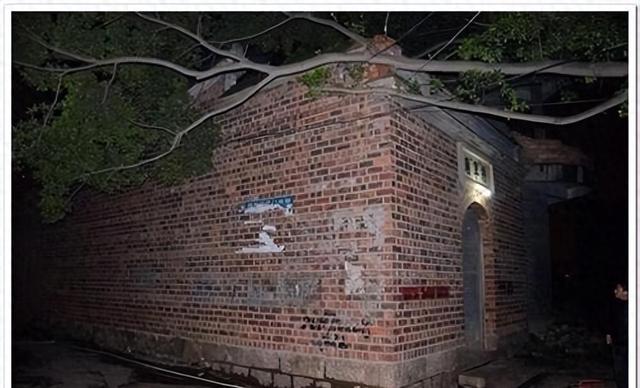
有些事情,说出来你未必信,但就这么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人们常说,世间无奇不有,有巧合也有命数。可倘若你亲历亲见,怕也得咂摸咂摸背后是不是还有点别的门道。清朝时候,就有这些边角余料的怪事,被一个姓潘的读书人给记了下来——讲出来,至今还叫人忍不住念叨两句。
潘伦恩。这名字你或许没听说过,他不是那种登堂入室的大人物,倒像我们身边那个念了书、心思多、路上瞅什么事都喜欢记两笔的中年人。可惜不巧,潘公活在个事多的年代,走南闯北求学,也就落下规矩,把见到的奇闻轶事写下来,算是聊以自慰,也留给子孙后代添几分谈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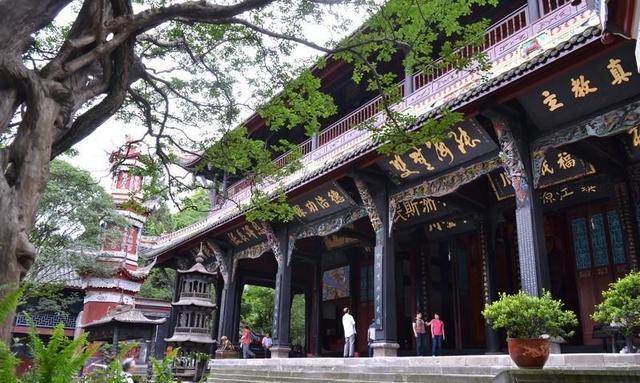
他的见闻里,头一桩便是乌泷坑的“鱼怪闹村”——听着玄乎,细品却透着点生活的烟火气。
那年潘伦恩出门游学,肚里早饿了三分,恰路过边远村落,主人家看他眉目清秀又带点书卷气,便留他小住两日。村里流的是一条浅浅的河,他刚掬了一把清水漱口,邻家大娘就送上鲜红的炖鱼。肉质弹牙,味蕾翻腾,潘伦恩夸了一句:“这鱼可真是人间难得的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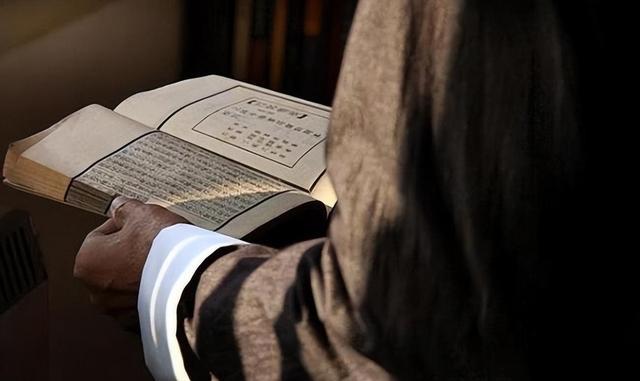
谁知当地的老人笑了,说潘公若早来几年,这点还不算什么。只有乌泷坑的鱼,才叫正宗。如今说起来,怕也只能咽口水了。
“咋就不能捞了?”潘伦恩琢磨着,有点刨根问底的架势。老人叹口气,那语气啊,像是在回忆一种失落的、再也回不去的丰饶,“鱼是原来的鱼,水不是原来的水了。”

老人细说当年——别看如今乌泷坑杂草丛生、泥泞不堪,早些年,那可是村里最灵秀的一潭。有水草的倒影,清澈得能见底,鱼虾多得奔腾如织。传闻里还有黑龙盘踞,说是庇佑一方的“龙潭”,谁家孩子做错了事,祖辈都要领着到潭边求平安。
可惜,转机就出现在咸丰二年。那日伙计们入潭打渔,网里竟拖上来一条不似寻常的鱼——浑身漆黑,偏还长了四只腿。你说怪不怪?村里人不敢下筷子,几个胆子大的小青年倒不信邪,说:“再怪也是鱼,怕它作甚!”—当场就是劈柴升火,锅里烹汤。

汤底咕嘟咕嘟,味道居然比平时还要香浓。他们就一边惊奇,一边撩起鱼腿切块,咋煮咋不熟。刀砍雷劈都不化,硬得像块石头。越琢磨越心里发毛,几人对视片刻,赶紧停了手,把剩下的鱼丢回河里,连锅带汤一同洗净,只当这事没发生。
可世事哪能就那么一笔抹消?第二天一早,天原本晴朗,谁知云头黑黢黢地压下,紧接着轰隆隆几声炸雷。冰雹噼里啪啦,漫天砸下来,田里的庄稼全毁了,还砸塌了好几间房,说是死人都不稀奇。短短一炷香的工夫,这天灾像是有意针对。“肯定是招惹不得的东西被吃了!”村里顿时人心惶惶。自那以后,乌泷坑就变了模样,原先的生气一点点褪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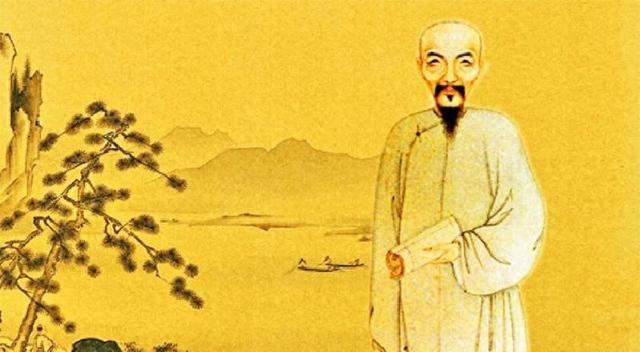
这些年,潘伦恩路过那片地,水色暗淡,泥沙填满,鱼腥味也淡得可怜。要不是亲耳听老辈人念叨,他大约也不会信,世上真有这种“劫数”缠着一村人。
但这古怪事,远不止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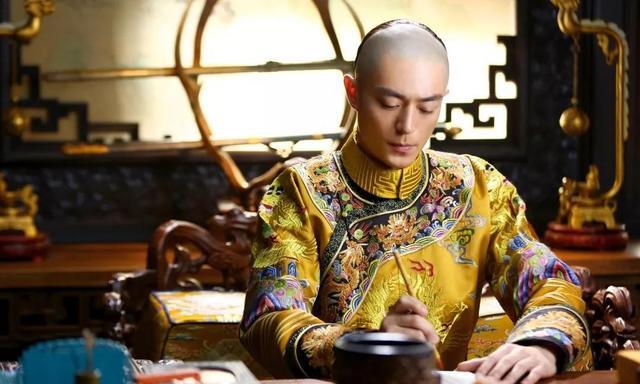
话还得往前跳。潘伦恩老家几十里之外,还有一村,那里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听说树龄比村里任何一位老人都要大几轮。每到夏天,树下凉风缕缕,孩子们在底下撒野,大人们则说,老槐撑着一村的风水,说不定还是个镇宅神物。
可人也好,树也罢,终究得服从自然的道理。谁料一日清晨,村民发现槐树枝叶枯得不成样子,树皮裂开大量口子。大家都当做老槐年纪太大——树顶多也就这么个数。可午后乌云压顶,一道天雷忽地下劈,把这根老槐从腰斩成了两断。天光恢复,众人本没太挂心,没想很快就传来四处轰动的事。

树一裂开,里面雪白雪白堆满蚂蚁尸体。成千上万,装了三只大筐还没清完。更稀罕的是,破碎树心里,窝着一块黑铁,坚硬如石,锈迹斑斑,把人难倒了。几个人折腾半天,用铁锤才敲松点,搅拌得泥里水里,还真扒出点门道来——说是蚂蚁在里面,竟建了座小小的蚁国:分着粮仓、兵营,小王朝似的,什么都有,各有门道,蚁王居中而坐,就差咬根牙签召见文武了。
这一发现,吓得人直拍大腿:“原来老槐不是自己枯死,是被蚂蚁一天一天吃空了命根子!”不过更让人纳罕的是,一场大雷把这些不讲理的小蚂蚁连窝带命全灭干净了,好像苍天也在伸手理一理秩序——谁鸠占鹊巢,谁就得收拾收拾。
说完这些事,我总忍不住想,人哪怕活得再精灵,终究是走在天地道理下头。潘伦恩记下这两桩事,说得不玄,就是想告诉后人:你可别光看表象,有时候天有天理,人有人情,做事要有分寸,连蚂蚁都不能胡来——否则结局怕比你想象的还要凄惨。
村口晒鱼的大爷至今还在述说乌泷坑早年的神奇,至于那棵成精似的老槐和蚂蚁的“宫殿”,早已化土归根。有时候,我也琢磨,那些年究竟是谁扰了谁的清净——到底是人动了龙潭的规矩,还是蚂蚁破了老槐的命数?这世界啊,细思极恐,也叫人有点敬畏。
若你路过乌泷坑,不妨停下来,看看河水,想想那些早已模糊的村民背影。哪怕什么也见不着,说不定放慢点脚步,心里能生起一点点对天地的敬重和谦卑。谁晓得呢?有些事,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