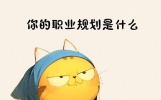在凌晨3时的寂静中,睡眠体检中心病房的走廊格外空旷。我轻步巡视病房,透过门上的观察窗,看到23床的王女士又在睁着眼睛望向天花板。这已经是她入院治疗的第5个夜晚了。
“还是睡不着吗?”我推门轻声问道。
她苦笑着摇头:“数了几千只羊,越数越清醒。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失眠‘吞噬’了。”
在睡眠科,这样的场景我见过太多。在传统认知中,睡眠障碍的治疗往往聚焦于药物干预和睡眠健康教育,但7年的临床实践让我深知,失眠从来不只是生理问题。
“如果不数羊,您现在的状态可以怎么形容?”我坐在王女士床边问道。
她沉思片刻:“像被困在一间没有门的房间里,四周是永无止境的黑暗,我能听见全世界安睡的声音,唯独自己被排除在外。”
“失眠对您做了什么?”我继续追问,并将问题和人分开,让患者意识到“我不是问题,失眠本身才是问题”。
随着交谈深入,王女士逐渐打开心扉。她是一名大学老师,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她逐渐失去了安眠的能力。“失眠像个小偷,偷走了我的精力、我的耐心,甚至偷走了我与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她看上去非常焦虑。
我鼓励她给失眠起个名字,她称之为“夜魔”。命名的过程让她第一次能站在失眠之外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与之融为一体。
“有没有‘夜魔’失手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晚上您睡得比较好?”我问道,并努力帮她寻找疾病问题中的一些例外,即叙事医学中的“特殊结果”。
王女士回想起来,上周五晚她睡满了5个小时:“那天女儿从学校回来,我们一起烘焙,说了很多贴心话……”
“那个时候,‘夜魔’为什么没能完全控制您?”我引导她思考。
“也许是因为我感到安心和快乐。”她眼睛微微发亮,“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放松。”
“夜魔”的力量变弱了
基于这次发现,我们开始共同重写她的失眠故事。我请她每天记录那些让“夜魔”力量变弱的小事:一杯温牛奶、一段轻柔的音乐、10分钟的冥想、与家人的亲密交谈……1周后,王女士的睡眠日记上开始出现积极的记录:“今晚‘夜魔’来得比较晚”“今天我只数了100只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后,我回忆起和女儿烘焙的快乐,居然又睡着了”……
更重要的是,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失眠的被动受害者,而是能够主动影响睡眠的主体。这种认知转变带来的力量,有时甚至比安眠药更有效。
在病房,我见证了无数像上述一样被改写的失眠故事。与此同时,我也惊讶于自己的护理经验被改变的过程。从前,我常常因为无法“治愈”患者的失眠而感到挫败。现在,我明白我的角色不是提供速效解决方案,而是陪伴患者,寻找他们内在的资源和力量。以往,我看待失眠主要依靠多导睡眠监测图上的数据和药物剂量。现在,我会倾听每个失眠背后的独特故事——那位失去老伴的老人,他的失眠是对思念的守夜;那位新手妈妈,她的失眠是母职焦虑的体现;那位高考生,他的失眠是对未来的恐惧……
每个失眠故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个讲述者都值得被尊重。我也逐渐明白:失眠不是一个需要被打败的敌人,而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信息。
现在,当患者对我说“我数了几千只羊还是睡不着”时,我会微笑着问:“那么,您愿意和我讲讲您的‘羊群’吗?也许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入睡而存在,而是想要告诉您一些重要的事情……”
从“数羊到入眠”的旅程,从来不是简单的直线距离,而是一段需要被倾听、被理解、被重写的生命故事。我也十分有幸成为这些故事的见证者和共写者。
文:武汉市武东医院睡眠体检中心 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