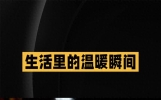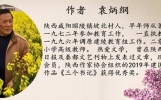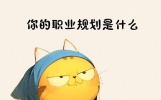打小在弄堂里长大,见惯了黄浦江的船来船往,听熟了吴侬软语的家长里短。总听人说青岛是"东方瑞士",心里头却犯嘀咕——海边的城,大抵都是潮乎乎的,能有什么不同?
这回带着爸妈和小女儿出门,本是想找个不那么挤的地方透透气。从上海飞青岛,才一个多钟头,落地踩上胶东半岛的土,倒真觉出些不一样来。这地方像块刚从海里捞上来的礁石,带着咸腥气,却也透着股结实的清爽。

印象一:海是活的,不像黄浦江那样憋着股劲儿
上海人见水不稀奇,黄浦江的水是深褐色的,载着货轮和游船,总像有忙不完的事。青岛的海却不一样,站在栈桥上往下看,水是分层的,近岸带点绿,往远了变蓝,再远就和天黏在一块儿,软乎乎的。
小女儿刚会跑,一到沙滩就疯了,脱了鞋往水里扎,浪花卷过来,她尖叫着往后躲,脚趾缝里嵌满金晃晃的沙。我妈在一旁叹:"这沙比外滩的细多了,踩上去像踩着棉花。"我爸蹲在礁石上,手里捏着个小铲子,说要给孙女挖蛤蜊,裤脚被浪打湿了也不恼,倒像个小孩儿似的乐。

傍晚在五四广场散步,海风裹着潮气扑过来,带着点海草的腥气。对岸的楼群亮了灯,不像陆家嘴那样挤得慌,倒像是撒在黑布上的珠子,稀稀落落的。女儿指着远处的灯塔喊"星星",我妈就给她讲"灯塔照路"的老话,我爸掏出手机拍海浪,说要发给他那帮老伙计,"让他们瞧瞧,这海比黄浦江敞亮"。
这海啊,不像黄浦江那样憋着股劲儿往前冲,它就那么慢悠悠地晃,涨潮退潮都有自己的性子,倒比上海的水多了几分自在。

印象二:老房子像留着胡子的老头,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上海的老房子是石库门,关着门是一家,开了门还是一家,墙缝里都透着烟火气。青岛的老房子却不一样,八大关的洋楼藏在树后头,红瓦尖顶,墙上爬满爬山虎,像些留着胡子的老头,不声不响地蹲在那儿。
带爸妈去花石楼,我爸摸着墙上的花岗岩,说这石头比外滩的纪念碑还硬实。讲解员说这楼住过不少大人物,我妈就凑到窗前往里瞅,"瞧瞧人家以前住的地方,窗台都雕着花"。小女儿在院子里追鸽子,石板路被踩得咚咚响,倒把那些沉在时光里的故事惊得活泛了些。

转到八大关的小路上,两旁的树把天遮得严严实实,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撒了些碎金子。有户人家的院墙上开着月季,红的黄的挤在一块儿,我妈忍不住站在花前拍照,说"这房子配这花,比弄堂里的晾衣杆好看"。
路过一栋德式老楼,门口坐着个老太太,手里织着毛衣,见我们看房子,就搭话:"这楼有百十年了,我嫁过来时,门槛比现在高半截。"她说着往屋里指,"里头的木地板,踩上去还咯吱响呢。"

这些房子不像上海的老洋房那样讲究排场,它们就那么安安稳稳地待着,墙皮掉了块,窗棂旧了些,倒比簇新的建筑多了些实在的温度。
印象三:海鲜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性子,鲜得直跳
上海人爱吃海鲜,菜市场的鱼虾也新鲜,但总隔着层水,像是养熟了的。青岛的海鲜却带着股野劲儿,刚从渔船上卸下来,在摊子上还蹦跶,眼里都透着活气。

早上去营口路市场,腥气扑面而来,比上海的水产市场浓多了。我爸拉着小女儿看梭子蟹,那蟹举着大钳子,把塑料盆夹得咔咔响。卖海鲜的大姐笑着说:"刚从沙子口拉来的,活泛着呢,给孩子买点虾虎,肉嫩。"
挑了些海蛎子、扇贝,旁边就有加工的小店,支着煤气灶,火苗呼呼地蹿。海蛎子蒸出来,壳一撬开,汁儿顺着指缝流,鲜得舌头都想吞下去。小女儿不爱吃葱姜,就那么白口吃,嘴角沾着汤汁,说"比上海的虾好吃"。我妈剥着扇贝,说这贝柱比超市买的大一圈,"人家这是现开的,能不鲜吗"。

中午在啤酒屋吃饭,老板推荐辣炒蛤蜊,说"青岛人夏天就指着这个下酒"。蛤蜊个个开口,汤汁红亮,带着点辣,鲜得直咂嘴。我爸抿着啤酒,夹起个蛤蜊,说"这鲜味,比清蒸鲥鱼还直接"。
这些海鲜不像上海宴席上的那样讲究摆盘,它们就那么实实在在地摆在盘子里,带着海水的咸,透着阳光的鲜,吃进嘴里,像把大海的味道嚼在了舌尖。

印象四:啤酒是渗在日子里的,比汽水还家常
上海的酒吧里,啤酒是装在玻璃杯里的,讲究个情调。青岛的啤酒却不一样,像自来水似的,拧开龙头就流,是过日子的东西。
在街头见人拎着塑料袋,里头装着黄澄澄的液体,我妈好奇,走近了看,是啤酒。卖散啤的大爷说:"青岛人夏天离不了这个,中午拎半袋,就着蛤蜊喝,舒坦。"

我爸忍不住要了一扎,刚倒出来,泡沫就漫了杯沿。他咂了一口,说"比瓶装的淡点,带着股麦香"。小女儿凑过来闻,被泡沫沾了鼻尖,咯咯地笑。老板见了,递过来个小杯子,"给孩子倒点,不含酒,尝尝味儿"。
傍晚在海边的排档,穿背心的大哥们光着膀子,面前摆着啤酒桶,杯子碰得叮当响。有个大哥见我爸喝得慢,就招呼:"来,碰一个!青岛啤酒,就得大口喝!"

这酒不像上海的精酿那样讲究口感,它就那么清清爽爽的,带着点苦,咽下去却回甘,像青岛人的性子,直来直去,却余味悠长。
印象五:青岛人带着海风的热乎,比空调还暖心
上海人客气,说话慢悠悠的,透着分寸。青岛人却不一样,热情得像夏天的太阳,直愣愣的,却让人心里熨帖。

在信号山公园问路,卖冰棍的大爷放下箱子,领着我们往山上走,"从这儿上去能看全景,红瓦绿树,比明信片上清楚"。他步子快,我妈跟不上,他就停下来等,说"老太太别急,咱慢慢走,顶上有石凳,能歇脚"。
在市场买海菜,摊主是个大嫂,见我不会挑,就一把把拣,"这个嫩,做海菜包子最好"。称完了,又抓了把虾皮,"给孩子熬粥,鲜得很"。我要多给钱,她摆手,"不值当,下次再来照顾生意就行"。

最暖的是在沙滩上,女儿的玩具铲子掉在水里,被浪卷远了。旁边一个捡贝壳的小男孩,二话不说扎进水里,把铲子捞了回来,浑身湿透了,咧着嘴笑,"给你,妹妹"。他妈妈在岸上喊他,"别着凉了",却也没怪他,只拿毛巾给他擦脸。
这热情不像上海的周到那样客气,它就那么实实在在的,不带半点虚礼,像海风一样,直接吹进心里,暖得踏实。

从青岛回来好些天,小女儿还总念叨着沙滩上的蛤蜊,我妈翻着照片说"那老房子真有味道",我爸则时不时说"该喝口青岛啤酒了"。
上海的日子是精致的,像精心摆盘的菜,每一口都讲究。青岛的日子却带着股海的粗粝,红瓦是红瓦,绿是绿,鲜是鲜,热乎是热乎,不藏着不掖着。

这地方像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海带,带着点咸,有点腥,晒晒干,却透着股子韧劲儿。
上海的老乡们,要是闷了,真该去走一走——看看那敞亮的海,摸摸那带故事的墙,尝尝那直来直去的鲜,感受感受那股子不绕弯子的热乎。毕竟日子嘛,有时候就得像青岛的啤酒,痛痛快快喝下去,才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