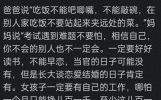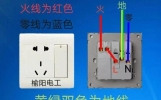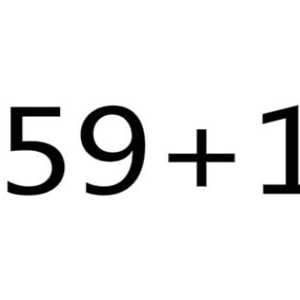124天。那段时间,她每天在中南海里读书、被打断、被追问,最后又带着一堆新的看法回北大。数字很简单,但对她来说,每一天都不一样。

最靠后的几天,聊天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本解释。有人记得有一次从《封神演义》谈到革命策略,把姜子牙的三样法宝比作某种现实操作的三项要素;又有一次把申公豹“回头看”的动作,用来讽刺倒退的思路。这样的联想不是随便说说,讲话的人能把古书里的细节和现在的事情连成线,逻辑清楚,力度又足。那会儿他走路慢,需要人搀扶,腿肿得厉害,气也不太好,但一坐下来谈书,声音里马上有了神采,问题也变得尖利,像是在做现场的学术“考核”。
往前推一个阶段,很多对话发生在半夜或清晨的紧急电话之后。她住处接到电话,骑着自行车赶去,院里灯光昏黄,走廊里人少。读的是《红楼梦》,讨论的是封建家庭的衰败,有句他当场背出来的诗句,被用来证明家道中落的细节。有人在场听着,会觉得像在听考题外的补充讲义:不是死背字句,而是把文本当成观察历史和社会的镜子。她当时把这些记下来,后来发现,很多当下的政治比喻就是从这些文本里来的。

更早些时候,第一次真正被他“考”是读《水浒》。她刚念完到宋江受招安的段落,对方立刻切入,把这部书评价为“好在投降”这种断言,又指出文本里把“聚义厅”改称“忠义堂”所含的政治意味,还能引出鲁迅的评论进行佐证。她愣住了——自己在这方面研究几十年,从没把书往那个方向解读过。那一次,她感觉到对方的阅读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而是把文学作为政治和历史的材料来剖析。
回到起点的那天,是1975年5月。北大西门外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把当时49岁的古典文学副教授芦荻接走。她以为只是在中南海念几首唐诗,没多想就上了车。平时她是考学生的人,熟悉唐诗宋词和四大名著,课堂上常常是主持讨论的那方。可这次角色互换,变成了被“审问”的一方。那辆车、那条路、那晚的光线,后来在她的记忆里都很清楚。

她之所以被请去,是因为主席视力受白内障影响,读书有困难。表面上请她来当侍读,实际上事情远比这复杂。陪读不是单纯念字就完了,更多是对话与辩证。每次读到某段,她会被打断,被要求解释为什么这样读,甚至被追问一些她自己也没深入考虑过的细节。对方会把文本里的微小地方当成切入点,连带引出对当下政策或历史的观点。她后来承认,那种问法逼得她不得不重新去看文本、去推敲每一句话的含义。
这些日子里,她见到的并不是一个只顾消遣的老人。虽然他有肺心病,腿部水肿,视力也在恶化,可一谈到古典文学就来劲,会精准背出句子来当证据,会突然引用其他作家的观点来铺垫自己的论点。对她来说,这种把读书当作思考工具的方式很新鲜,也很震撼。她自己常说,那124天的收获,超过了她几十年的课堂经历。

在日常细节上也有很多小事:她有时在院子里坐着记笔记,把讨论的片段写成条目;有时站在窗边听对方把一句诗拆成好几层来讲;有时在走出中南海时,天还没亮,空气里冷冷的,手里捏着一页抄下的句子,脑子里却在反复琢磨那些被提出的隐含意义。她开始觉得,这种读书不是为了学问的虚荣,而是一种把历史经验用来理解现实的实操法门。
整个过程并非没有摩擦。她也有抵触和不解,觉得有些解读出乎意料;有时被质疑教材里的标准说法,会觉得不舒服。但对方的逻辑往往能把问题越推越深,让她不得不回到原文去验证自己的看法。一次次被追问,让她把看似熟悉的段落重新看了又看,发现以前的教学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

那段时间结束后,她把记录带回学校,课堂上对学生表达方式的调整能明显看出受了那几个月影响。结束的那天,院子里安静,她合上笔记本,把散乱的纸张摞好,走出中南海,骑回去的路上天色才亮。她没有大声宣布什么,也没写公开的总结,只是把那些天的对话放在心里,偶尔在课堂上把某个片段提出来,像是把借来的视角还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