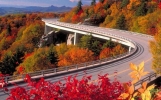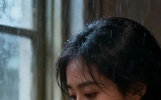你记得那片芦苇荡吗?

二十年前没人敢走近,现在成了候鸟的家,也成了孩子们的课本。

苏婉娘没死在风言风语里,她活成了村口那棵老柳树——根扎得深,枝叶却从不遮天。
她编的芦苇席子,如今摆进了博物馆,旁边那把锈了的镰刀,是她凌晨四点下地时用的。
没人再提她守寡的事了,可她自己还总说:“日子不是别人说的,是你弯腰一镰一镰割出来的。
”
李家坳的小学,以前连粉笔都得省着用,现在有奖学金了,名字就叫“芦苇”。
五十块能买一袋米,五千块能送一个娃去大学。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是她偷偷塞了三年鸡蛋换来的学费。
如今那孩子在杭州当老师,每年回来都蹲在她门口,陪她编席子,不说话,就听芦苇摩擦的沙沙声。
你猜怎么着?
当年骂她“克夫”的李大爷,孙子女李娟,去年当上了妇女互助会会长。
她们在村口搭了个小棚子,教姑娘们编灯笼、做粽子,不收钱,只问一句:“你怕不怕别人说?
”没人答,但手没停。
黄河水还是黄的,可岸边的芦苇不再被烧掉当柴火了。
政府立了牌子,说这是生态湿地,可村民知道,那是苏婉娘用半辈子换来的。
她不说话,就天天去巡,看有没有人偷挖芦苇根,看有没有小孩往水里扔塑料瓶。
前年拍纪录片的记者问她:“您后悔吗?
”她低头把一束芦苇捆紧,抬头笑了:“后悔啥?
我活成了这片地,地活成了我。
”
现在去李家坳,你会看见年轻妈妈们带着娃在芦苇丛边拍照,孩子指着白鹭喊“鸟鸟飞”,妈说:“那是你太奶奶当年守过的。
”
没人再提寡妇两个字了。
可你要是蹲在河边,听风穿过芦苇的响,就知道——有些东西,从来不是靠口号活下来的。
是有人,把日子嚼碎了,咽下去,然后长成了土地。